《迷霧之子:執法鎔金—謎金》楔子、第一章與第二章試讀 Read The Lost Metal: Prologue and Chapters One and Two
楔子
偉恩知道關於床的知識。錫重聚落(Tinweight Settlement)中其他孩子有。一張床聽起來比地板上的毯子好多了——尤其是在那些寒冷的夜晚。那時他必須與老媽(Ma)共用毯子,因為他們沒有煤。
而且床下有怪物。
是啊,他曾聽過霧魅的故事。他們會藏在你的床底下偷走你認識的人的臉。所以床上面軟綿綿的,底下則有你可以聊天的東西?聽起來就是鐵鏽的天國。
其他孩子害怕霧魅,但是偉恩覺得他們只是不懂如何正確地與其溝通。他可以與住在床底下的東西做朋友。只要給它某些它想要的東西就好,像是給它吃的其他人。
不管怎麼樣,反正他沒有床。也沒有真正的椅子。他們家有一張桌子,是格雷格(Gregr)叔叔製作的。他隨後就在一次土石坍塌時被數十億塊岩石粉碎,壓成一攤肉泥。至少他沒辦法再打人了。偉恩不時就會去踢一踢桌子,以防格雷格的靈魂仍偷偷從某處關注然後找到它。在這小小的、單窗的家中,鐵鏽曉得除了這東西外還有什麼是格雷格叔叔關心的。
最適合偉恩拿來坐的是一張凳子,所以他坐上去,一邊等著一邊玩著他的牌——在發牌的同時藏牌進袖子裡。這是一天中的一個緊張時刻。每個傍晚他都害怕也許她不再回家。不是因為她不愛他。老媽可是世界這坨汙泥中綻放的甜美鮮花。但因為老爸(Pa)有天就不再回家。格雷格叔叔——想到這偉恩就踢了一下桌子——也是有天就不再回家。所以老媽……
別想了。偉恩想,同時他笨手笨腳地將正在洗牌的牌疊灑到桌上地上到處都是。也別看。看到光前都不要。
他也許能去探探外頭礦坑。沒人想住礦坑邊上,所以偉恩與他老媽就住下了。
他故意開始想其他事。牆邊有一堆當天先前偉恩洗好的衣服。那是他老媽薪水不太夠的老工作。現在她去推礦車時他來做這個。
偉恩不介意這項工作。可以試穿所有各式各樣的衣服——不論是老爺子的到年輕女人的,然後假扮成他們。他老媽抓到他幾次過,生氣罵他。她的惱怒至今仍使他疑惑。怎麼不全拿來試穿看看呢?衣服就是拿來穿的啊。又不是甚麼怪異的舉動。
而且,有些人在口袋裡留了一些玩意兒。像是一套卡牌。
他繼續笨拙地洗牌。他著手收整撒落的卡牌時就不看著窗外,儘管礦坑還是在繼續干擾他的心神。那個大開的洞口向外噴出如血如火的紅色光線,就像脖子上的大口子。老媽必須在那野獸的內部挖掘、尋找金屬,然後逃離它的怒火。人並不能永遠都那麼幸運。
然後他看到了。有光。他不再緊張害怕,瞥了窗外一眼,看到有人提著燈籠沿路走來。偉恩驚慌地把卡牌藏到毯子下,然後躺在上面,在門打開時假裝睡著。她當然早就看到剛剛還亮著的光了,但她欣賞他為假裝做出的努力。
她在凳子上坐下,偉恩一隻眼睛偷偷睜開一小點縫偷看。他老媽穿著長褲與鈕扣襯衫,頭髮綁起來,衣服與臉都一片髒。她坐著,呆呆盯著燈籠裡的火焰,看著它閃爍舞動。她的臉看起來比以前更加凹陷。像是有人拿著十字鎬搞她的臉頰。
那個礦坑正吃了她。他想。不像老爸那樣一口吞掉,但也是慢慢地啃食。
老媽眨了眨眼,然後注意到了其他某個東西。他留在桌上的卡牌。噢,完了。
她將它拿起,然後直直看著他。他不再假裝已經入睡。她會往他身上倒水。
「偉恩,」她說。「你從哪裡拿到這些卡牌?」
「不記得。」
「偉恩……」
「找到的。」他說。
她伸出手,他只好不情願地將牌組拉出來交上去。她將她找到的卡牌收進盒子裡。該死的。她會花上一天尋找錫重裡誰「遺失」東西。他不想讓她因他失去更多的睡眠時間。
「塔克.魏斯丁道(Tark Vestingdow)。」偉恩小聲咕噥。「工作服的口袋裡。」
「謝謝。」她溫和地說。
「媽,我要學牌。那樣我能多少掙點好生活。」
「好生活?」她問。「靠牌?」
「別擔心。」他很快地回應。「我會作弊!沒贏了話怎麼討生活,懂嗎。」
她嘆了口氣,揉著太陽穴。
偉恩瞥一眼那疊卡牌。「塔克。」他說。「他是個泰瑞司。跟爸一樣。」
「對。」
「泰瑞司人總是照著他們被告知的方式做事。為什麼我就不一樣?」
「寶貝,你沒有錯。」她說。「你只是沒有一個足夠有力的親人去指引你。」
「媽。」他說,並一邊凌亂倉促地爬出毯子抓住她的手臂。「不要那樣說。你是最偉大的媽。」
她將他攬到身旁。他能感覺到她的緊繃。「偉恩,」她輕聲詢問。「你有拿走戴米(Demmy)的小刀嗎?」
「他說的?」偉恩說。「鏽他鐵鏽的雜種!」
「偉恩!不可以這樣罵人。」
「鏽他鐵鏽的雜種!」他改用鐵路工的口音說。
他天真地向她微笑,得到一個她藏不住的笑容。滑稽的聲調總是能讓她開心。老爸以前擅長這個,但偉恩更強。尤其現在老爸死了沒辦法再說了。
但是她的笑容隨即消褪。「偉恩,你不能拿走不屬於你的東西。這是小偷才會做的事。」
「我不想當小偷。」偉恩輕聲說,把小刀放在卡牌的旁邊。「我想當好孩子。但是它就是……發生了。」
她更緊地抱住他。「你是好孩子。永遠是個好孩子。」
她說的話他都相信。
「親愛的,你想要聽故事嗎?」她問。
「我已經長大,不聽故事了。」他說謊,他其實非常希望她說一個。「我十一歲。再一年我就可以在酒館喝酒了。」
「什麼?誰跟你說的?」
「德格(Dug)。」
「德格才九歲。」
「德格懂事。」
「德格才九歲。」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明年得幫他帶點酒,因為他不能自己買嗎?」他對上她的眼睛,然後開始偷笑。
他幫她準備晚餐——加豆子的冷燕麥粥。至少不是只有豆子。然後他縮進墊子上的毯子中,假裝他還是個孩子,準備要聽故事。這裝起來很簡單。畢竟他還有那些衣服。
「這一個故事,」她說,「主角是不洗澡的強盜巴雷特.巴姆(Blatant Barm, the Unwashed Bandit)。」
「哇噢……」偉恩說。「一個新故事?」
他的母親傾身向前,一邊說話一邊指著他揮了揮湯匙。「偉恩,他可是他們當中最糟的一個。最壞、最卑鄙、最臭的一個強盜。他從不洗澡。」
「因為要弄得髒兮兮需要先花大把的力氣?」
「不,是因為他……等等,弄髒需要花大把力氣?」
「必須在裡頭滾來滾去,懂吧。」
「老和諧啊,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要學當地板。」偉恩說。
「要……」她笑了。「噢,偉恩。你真的是我的寶貝。」
「謝謝。」他說。「如果巴雷特.巴姆真的這麼壞,為甚麼以前你沒說過?難道不應該是你跟我說的第一個故事嗎?」
「你那時太小,」她說,一邊回復原本坐姿。「而這個故事太可怕。」
噢噢噢……這會是個好故事。偉恩跳上跳下動來動去。「誰抓到伊?執法者?」
「是鎔金賈克。」
「他?」偉恩呻吟。
「我以為你喜歡他。」
所有小孩都喜歡。賈克新奇有趣,而且過去一年解決各種不同的困難案件。至少德格這麼說。
「但賈克總是吸引壞人來。」偉恩抱怨。「他從來沒開過一槍。」
「這次不一樣,」老媽說,並挖了一湯匙麥片。「他知道巴雷特.巴姆是最壞的那種人。絕對凶神惡煞。甚至巴姆兩個嘍囉——殺手古德(Gud the Killer)和無情約依(Noways Joe)——都比任何其他曾行走於蠻橫區的盜匪壞上十倍。」
「十倍?」偉恩說。
「嗯。」
「那很多欸!幾乎相當於乘二了!」
他老媽皺眉了一下,但隨即再次傾身向前。「他們搶了薪資名冊。不只從依藍戴裡的肥羊身上奪走錢,連普通人的薪水也不放過。」
「雜種!」偉恩說。
「偉恩。」
「好!那就一般的老敗類!」
她又遲疑了。「你……你知道『雜種』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嗎?」
「用來指一種敗類,大概是當你停留太久真的必須走時,別人會用來叫你。」
「你知道的原因是……」
「德格說的。」
「當然是他。總之,賈克,他不能容忍從蠻橫區普通人身上偷東西這件事。成為強盜是一回事,所有人都知道你搶的是向城市流動的錢。
「不幸地,巴雷特.巴姆,他非常熟悉這個地方。所以他騎馬深入蠻橫區最難找的土地,他還在沿途上的關鍵地點留下一個嘍囉來看守。幸運的是,賈克是最勇敢的人。也是最強的。」
「如果他是最勇敢最強的,」偉恩說。「他為什麼要當執法者?他可以去當強盜,而且沒有人能阻止他!」
「寶貝,哪個比較難?」她問。「做對的事和做錯的事?」
「做對的事。」
「所以誰比較強?」老媽問。「做簡單的事的傢伙,還是做困難的事的人?」
啊。他點頭。對。對,他懂了。
她把燈籠移近臉旁,使其隨說話搖曳閃爍。「賈克的第一個考驗是人類河(River Human),那條寬廣的水道標明克羅司曾經的領土邊界。迅疾的水以火車的速度流動,它是全世界最快的河,而且裡面都是石頭。殺手古德在河對岸駐紮,來監視執法者。他的好視力與沉穩的手讓他可以在三百步外射下人旁邊的飛蠅。」
「為什麼要這樣做?」偉恩問。「射下飛人不是更好嗎?這樣可以消滅一些怪東西。」
「飛蠅不是在飛的人,寶貝。」老媽說。
「所以賈克怎麼辦?」偉恩問。「他躲起來嗎。躲起來不像是執法者。我覺得他們沒有這樣做過。我賭他沒有躲起來。」
「欸……」老媽說。
偉恩緊抓毯子等待著。
「賈克的槍法更好。」她低聲說。「當殺手古德看到他時,賈克已經先射中了,雙方還隔著整整條河。」
「古德怎麼死的?」偉恩低聲說。
「被子彈射死的啊,寶貝。」
「正中眼睛?」偉恩說。
「應該吧。」
「古德抬手時賈克也照做——但賈克先射擊了,直接沿著古德的視線射進他的眼睛擊中古德。是吧,媽!」
「嗯哼。」
「他的頭爆開,」偉恩說。「像鮮脆的水果,殼硬但內部軟黏的那種。是這樣嗎?」
「當然。」
「哭枵啊,媽。」偉恩說。「這很可怕。你確定你跟我說這個故事沒問題嗎?」
「我要停下來嗎?」
「當然不!賈克怎麼過河的?」
「他飛過去,」老媽說。她將燕麥粥吃完的碗放到一旁,雙手動作誇張地揮了揮。「使用他的鎔金力量。賈克可以飛、跟鳥說話還有吃掉石頭。」
「哇。吃石頭?」
「嗯哼。所以他就飛過河。但下一個挑戰更困難。死亡峽谷(Canyon of Death)。」
「噢噢噢……」偉恩說。「我賭那個地方很漂亮。」
「你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除了很漂亮之外不會有人要去叫做『死亡峽谷』的地方。但有人去了,而且我們也知道這個名字。所以一定很漂亮。」
「美麗。」老媽說。「一個峽谷從中切穿一堆瓦解的岩石尖峰、破碎山峰點綴著色帶,像是畫上去的。但這個地方就跟它的美麗一樣致命。」
「耶,」偉恩說。「想像出來了。」
「賈克沒辦法從這上面飛過去,因為第二個強盜藏在峽谷裡。無情約依。他是手槍的大師,也會飛,還會變成龍,還會吃石頭。如果賈克試著溜過去,約依會從他背後射中他。」
「這是一種聰明的射擊方法。」偉恩說。「他們就沒辦法還擊了。」
「確實。」老媽說。「所以賈克不會讓這樣的事發生。他必須走進峽谷裡——但那裡滿滿都是蛇。」
「血腥地獄啊!」
「偉恩……」
「那就,一般的老無聊地獄啊!有多少蛇?」
「一百萬隻。」
「血腥地獄啊!」
「但賈克,他很聰明。」老媽說。「所以他想到要帶一些為蛇吃的食物。」
「一百萬份的蛇飼料?」
「不,只有一份,」她說。「但他讓蛇為了爭那一份打架,所以他們幾乎殺光彼此。然後當然的,留下來的那一隻是最強的。」
「當然。」
「所以賈克就叫它去咬無情約依。」
「所以約依就變成紫色!」偉恩說。「然後耳朵流血!他的骨頭被融掉,所以從鼻子裡流出融化的骨水!他變成一坨乾癟的皮膚倒下,一邊發出嘶聲與大哭,因為他的牙齒被融掉了!」
「確實。」
「哭枵啊,媽。你說了一個最棒的故事。」
「後面更精采,」她溫和地說,靠在凳子上,他們的燈籠快燒盡了。「因為結局還有一個驚喜。」
「什麼驚喜?」
「一旦賈克通過現在聞起來像是死蛇與融化骨頭的峽谷,他面對最後一個挑戰:孤獨高地(Lone Mesa)。在一大片平原中央的巨大台地。」
「這不是什麼挑戰,」偉恩說。「他可以飛到上面。」
「他嘗試了,」她低聲說。「但高地就是巴雷特.巴姆。」
「什麼?」
「沒錯,」老媽說。「巴姆成為了克羅司——是變成巨大怪物的那種,不是像諾克(Nock)老太太那樣正常的。他們教他如何變成巨人尺寸的怪物。當賈克嘗試降落時,高地把他一口吞掉了。」
偉恩倒抽一口涼氣。「然後,」偉恩說。「它用牙齒一口咬住他,粉碎他的骨頭——」
「不,」老媽說。「它試著吞下它。但是賈克,他不只聰明善射。他還有其他的東西。」
「什麼?」
「該死的超令人討厭。」
「媽!那是髒話。」
「在故事裡沒關係。」老媽說。「聽著,賈克是一個刺頭。他過去總是做好事。幫助人們。讓壞人不好過。古道熱腸。他知道如何破壞強盜的生活。
「所以被吞下後,他伸出手腳,用力一推,讓自己成為巴雷特.巴姆喉嚨的一根刺,讓怪物不能呼吸。像這樣的大怪物需要很多空氣。如此,鎔金賈克成功從裡面噎死巴姆。然後,當怪物倒在地上死去時,賈克從它舌頭上悠閒地走下來——就像有錢人從馬車走出來到外面的豪華地毯上。」
哇。「那真是一個好故事,媽。」
她微笑。
「媽,」他說。「這個故事是……關於礦坑的嗎?」
「這個嘛,」她說。「但我想我們所有人時不時都要走進野獸的嘴巴裡。所以……也許也是吧,我猜。」
「那你就像執法者。」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執法者,」她說,吹熄燈籠。
「即使是我?」
「尤其是你。」她親了一下偉恩的額頭。「偉恩,你是你想成為的任何東西。你是風。你是星。你是世上無盡萬物。」
這是一首她喜歡的詩。他也喜歡。因為是她說的,所以他相信。怎能不呢?老媽不說謊。所以,他依偎進毯子裡讓自己入睡。世界上有很多事是錯的,但有些事還是對的。只要她在身邊,故事就有意義。他們都是真的。
直到隔天,礦坑裡又發生一次崩塌。那晚,他老媽沒有回家。
第一章
二十九年後
瑪拉席以前從來沒進下水道過,但這確實與她想像得一樣糟糕。理所當然地,氣味臭不可聞。但最糟的是她穿靴子的雙腳時不時就令人心跳驟停地滑一下,威脅要讓她一頭栽進底下的「泥漿」裡。
至少她今天有先見之明穿上褲裝制服和及膝皮革工作靴。但那些不能遮擋住氣味、感覺,以及最糟糕的,聲音。當她一手拿地圖另一手提步槍踏出一步時,兩隻靴子抽出泥漿時都會伴隨著音量詭異的吧唧聲。那有機會成為最糟糕的聲音,只不過偉恩的抱怨聲戰勝它奪得第一。
「瓦從來不會帶我到鐵鏽的下水道,」他舉著燈籠嘟囔。
「蠻橫區有下水道?」
「好吧,沒有,」他承認。「但牧場聞起來幾乎一樣糟,他帶我行進穿越那些地方過。但瑪拉席,那裡可沒有蜘蛛。」
「很可能有,」她說,一邊把地圖斜向他的燈籠。「你只是看不到。」
瑪拉席朝著側邊隧道點點頭,他們開始朝該方向移動。「你想聊聊那個嗎?」
「哪個?」他要求解釋。
「你的情緒。」
「我鐵鏽的情緒一點問題也沒。」他說。「這就是當你的搭檔強迫你去把自己顏面插進一坨從身後排放出來的東西時可以精準預期的情緒。」
「上週,」她問,「當我們調查香水店時?」
「鐵鏽的調香師。」韋恩說,他瞇起眼睛。「沒人知道在那些夢幻氣味下他們隱藏了什麼。你不能相信一個聞起來不像男人的男人。」
「汗與酒?」
「汗與廉價的酒。」
「韋恩,你怎麼會抱怨用空氣來裝扮的人?你每次都用換帽子來裝扮成不同人物。」
「我的味道有改變嗎?」
「我想沒有。」
「爭論勝利。論點完全沒有任何漏洞。討論結束。」
他們交換一個眼神。
「我應該找些自己的香水,是嗎?」韋恩說。「如果我總是聞起來像是汗與廉價的酒,有些人或許能識破我的易容。」
「你沒救了。」
「真正沒救的,」他說,「是我可憐的鞋子。」
「可以穿靴子來,就如我之前建議的。」
「沒靴子。」他說。「瓦偷走了。」
「瓦偷走你的靴子。真的啊。」
「嗯,他們在他的壁櫥裡。」韋恩說。「反而是他三雙最時髦的鞋子不知道為什麼出現在我的壁櫥,完全純屬偶然。」他偷喵她一眼。「這是公平交易,我可是很喜歡我的靴子的。」
瑪拉席微笑。自瓦在悼環的發現後退休,他們倆到現在已經一起工作幾乎六年了。偉恩成為官方保安官,而不再是某種程度上代表著灰色地帶的公民。他甚至穿起制服一次過。而且——
——而且瑪拉席的靴子又打滑了。鐵鏽地獄啊。如果她失足,他絕對會笑個不停。而且這大概是最好的結果。整個城市地下鐵路隧道的建設正在進行,兩天前一名爆破技士提交一份蹊蹺的報告。他不想要炸開下一個區段,因為震波讀數標明他們靠近一個未測繪的洞穴。
依藍戴市這地區的地下充斥著古老洞穴。這區域也是當地幫派執行人反覆消失蹤影又再出江湖的地方。就像是他們有著通往未知未聞巢穴的隱藏入口。
她再次確認地圖,上面標記著工程筆記——以及標明附近古怪的更古老註釋,那是下水道建造者數年前紀錄但從未調查過的。
「我想宓蘭準備要跟我分手,」韋恩輕聲說。「這可能是為什麼我最近性情反常的悲觀。」
「你為什麼這麼認為?」
「因為她告訴我:『偉恩,我幾週內可能必須與你分手。』」
「嗯,這是她的禮貌。」
「我認為她從大頭那裡得到新工作。」偉恩說。「但這不對,過程太慢了。不是與男人分手的適當方式。」
「那怎麼樣才是適當方式?」
「朝他的頭丟些東西。」偉恩說。「賣掉他的物品。告訴他夥伴他就是個膦屌。」
「你曾有過一些有趣的人際關係啊。」
「不,只是一堆糟糕的關係。」他說。「我問潔米.沃爾斯(Jammi Walls)她覺得我該做什麼——你認識她吧?她大多數晚上都在酒館。」
「我聽過這人。」瑪拉席說。「她有點……聲名狼藉。」
「什麼?」偉恩說。「誰說的?潔米的風評極佳啊。在街區裡所有的妓女中,她提供最好的——」
「不需要告訴我接下來這部分,謝謝。」
「聲名狼藉。」他竊笑。「我會告訴潔米是你瑪拉席說的。她可努力經營著她的名譽。價碼可是其他任何人的四倍欸。太聲名狼藉了吧。」
「總之她到底怎麼說?」
「她說宓蘭想要我更努力經營關係,」偉恩說。「但我覺得這次潔米說錯了。因為宓蘭不耍小心思。她可是說一不二。所以這次……你懂得……」
「我很遺憾,偉恩。」瑪拉席說,把地圖夾在胳膊下並把空出來的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早就知道不能長久。」他說。「鐵鏽的知道,你懂嗎?她大概,怎麼說,一千歲吧?」
「其實數字約略是你說的三分之二。」瑪拉席說。
「但我連不惑之年都遠遠不到,」偉恩說。「如果你算上我青春的肉體還更像是十六歲。」
「以及你的幽默感。」
「該死的就是。」他語畢嘆了口氣。「最近生活……變得很難。瓦跟著上流階級去混了、宓蘭一離開就是好幾個月。感覺我沒人要了。也許下水道就是我的歸宿,你懂吧?」
「你不要這樣,」她說。「你是我曾有過最好的夥伴。」
「唯一合作過的夥伴。」
「唯一?勾爾格倫(Gorglen)不算嗎?」
「不。他不是人類。我找到一份論文證明他其實是易容過的長頸鹿。」然後他露出微笑。「但是……謝謝你問了。謝謝你的關心。」
她點頭,然後領路前行。當她想像著作為頂尖警探與執法者的人生時,她從未預期到這個。至少氣味問題感覺逐漸好轉——或著是她開始習慣了。
在地圖上標記的確切地點上,能找到下水道牆面上的一扇老舊金屬門,這成果令人非常滿意。偉恩舉起燈籠,就算沒有偵探的敏銳雙眼也能看出這扇門經常被使用。門框的一側有著銀色刮痕、門把乾淨而無污穢與蛛網。
建造下水道的人發現了這個,並強調是可能具有歷史意義的地點。但筆記卻因為官僚階層體制的荒謬而丟失。
「讚,」偉恩靠向她。「一流偵探啊,瑪拉席。你讀了多少舊調查才找到這個?」
「可太多了,」她說。「人們一定會很意外有多少的時間是花在文件庫裡的。」
「他們總是從故事中刪了前置研究。」
「你在蠻橫區做過這種事?」
「欸,蠻橫區特化版本的,」偉恩說。「通常包含壓某張腫成豬頭的臉進水槽直到他想起他順手牽羊過哪份舊墾照,不過原則上相同啦。噢,有更多的咒罵。」
她把步槍交給他然後開始調查門。他不喜歡她小題大作,但他近來已能握住槍而手不抖了。她還是不曾看過他開過一槍,但他說如果必要時他可以。
門緊關且在這側沒有鎖。但似乎她正在追獵的人也遇上關著的門——門板一緣有許多痕跡。有足夠的空間塞東西進門板與門框之間。
「我需要刀子搞定這個。」她說。
「我可以借你我如剃刀般銳利的智巧。」
「唉,偉恩,你不是我此刻需要的那種工具。」
「哈!」他說。「我喜歡這句。」
他從背包中拿出一把刀子遞給她,那裡面還有一 些補給,像是繩索以及面對金屬之子時可能用得上的金屬。這種層級的幫派不應該有鎔金術者(Allomancer)——他們只是最基礎「勒索店主討要保護費」的那一類。然而她收到的報告使她警惕,且她越來越確定這個團體受到「集合」組織(the Set)的資助。
「集合」組織 the Set:官方翻譯為「組織」,但目前可確認作者使用此詞彙有數學名詞「集合」的意思,下文簡單譯為集合
已經過了幾年,她還在追尋答案,這個問題從她執法者職涯的開始就困擾著她。那個被稱為集合的組織,曾以為由瓦的叔叔愛德溫所運營,後來又揭露出他姊姊泰爾欣(Telsin)也有涉入。一個跟隨、崇拜並推動一個被稱為特雷的幕後黑手所規劃的詭計。一尊神,她想。來自於古老世紀。
泰爾欣 Telsin :官方翻譯為「黛兒欣」,但根據泰瑞司人名的翻譯方式(把Te音節翻譯成泰),以及在本書中的一些設定爆點,個人認為泰爾欣這個翻譯更為合適。暴雷內容反白注意:泰爾欣是泰爾丹(Taldain)上名為自主(Autonomy)的碎(Shard)為了入侵司卡德利亞計畫所化出的降世化身(Avatar)
如果她抓到對的人,她可能最終可以得到答案。但她不斷的功虧一簣。最接近答案的一次是六年前,但他們捕獲的所有人——包含瓦的叔叔——都在爆炸中喪生。留下她繼續追趕著幽影,而其餘的依藍戴菁英則完全致力於忽視威脅。因為沒有證據,她和瓦甚至沒法證明在艾德溫一黨人死後集合仍舊存在。
使著刀,她設法解開從另一側插上的門閂。門閂隨著輕聲一響噹啷鬆脫,然後她小心翼翼推開門,現出一條粗糙開鑿的隧道向著下方延伸。通往神話與英雄的世紀,通往灰落與暴君的紀元。
她與偉恩兩人一同溜進裡面,只留下所找到的門。他們調暗燈籠作為預防措施,然後開始向著深處前去。
第二章
「領巾?」史特芮絲看著清單讀道。
「繫好別住了。」瓦一邊說一邊拉緊。
「鞋子?」
「擦亮了。」
「第一條證據?」
瓦拋了一個銀色獎章到空中,然後再一把抓住。
「第二條證據?」史特芮絲在清單上做了註記並繼續問。
他從口袋拉出一小疊摺起來的紙。「這裡。」
「第三條證據?」
瓦檢查另一個口袋,然後停頓住,環顧小辦公室四周——這是他在會議院(House of Proceedings)的參議員辦公室。他把東西遺留在……「在家裡的書桌上,」他懊惱地敲了敲自己腦袋。
「我有帶備用的。」史特芮絲開始翻找她的袋子。
瓦微笑。「你當然有帶。」
「事實上,兩份。」史特芮絲交給他一張他亂塞到不見的紙。然後她繼續查閱清單。
小瑪希黎恩(Maxillium)也在他母親旁照做,試圖表情嚴肅地掃視他自己的塗鴉清單。
「狗狗的圖。」瑪開口了,好像是從他的清單上讀出來的。
「我可能需要一張。」瓦說。「相當有用。」
瑪慎重地呈上一張,然後說:「貓咪的圖。」
「那也要一張。」
「我不會畫貓咪,」瑪說,遞出另一張紙。「所以看起來像松鼠。」
瓦抱抱他的兒子,然後嚴肅地把紙與其他幾張收在一起。這男孩的妹妹廷朵(Tindwyl)——史特瑞西喜歡傳統名——在角落牙牙學語,女家庭教師凱絲(Kath)則看管著她。
終於,她把手槍接續遞給他。他們具有長槍管且有重量感,拉奈特是為了視覺上的威嚇感設計,不過他們具有兩個保險且此時已退膛。自從他上次需要射擊人已經過了相當時間,但他還是持續的善加利用「蠻橫區的執法者參議員」這個渾號。市民們,尤其是政治人物們,小小的武器就能讓他們退縮。他們更偏好使用更現代的武器殺人,譬如說貧窮與絕望。
「清單上有給妻子一個吻嗎?」瓦問。
「事實上,沒有,」她驚喜地說。
「罕見的疏漏啊。」他說,然後長吻她一下。「今天上台的人應該是你才對,史特芮絲。妳比我還準備充足。」
「你是家主。」
「我可以指派你為發言代表。」
「拜託,別。」她說。「我在人前的表現你心知肚明。」
「在對的人面前的表現就很好啊。」
「那你說政治人物與對之間有任何一丁點的關係嗎?」
「我希望有啦,」他說,一邊拉直套裝大衣並轉向門口。「因為我就是一個。」
他離開辦公室下到參議會的樓層。史特芮絲則會從觀景台的專屬座位觀看——到今日,所有人都知道她對於同一個座位有多堅持了。
當瓦踏入寬敞的議堂,裡面正因為從短暫休會回歸的參議員們而熱鬧非凡,他沒有直接到他的位子。在過去幾天,參議員針對當前法案已進行討論,而他會是最後一個發言。他為了確保這個位置給出許多承諾與許多利益交換,他只希望這可以給他的主張一些優勢,給他阻止一項糟糕決定的最好機會。
他站在發言人講台的一側等待所有人就坐,他的拇指勾在槍帶上表現備戰姿態。在蠻橫區你會學到審問囚犯時的威嚇方法,到現在他仍訝異於有如此多的技能在這也適用。
瓦爾倫斯(Varlance)總督沒有看著他。那個男人擺弄著領巾,然後檢查臉上的化妝粉——因為一些奧妙的理由,鬼一樣的蒼白是近來的流行。然後他把獎章一個一個排放到桌上。
鐵鏽的,我想念亞拉戴爾。瓦心想。近來出現稱職總督都變成新鮮事了。就像……吃著旅館食物然後發現那原來還不算糟糕一樣,或是與偉恩廝混然後發現懷錶還在身上。
不過,總督的工作就是會讓好人累倒但讓壞人自在的那種類型。亞拉戴爾在兩年前卸任。而與南方大陸(Southern Continent)的緊張態勢使選擇軍方出身人士為下一任總督看來合理。新發現國家的人民——他們有著飛船與奇怪面具——仍然對於六年前的結果不滿。具體來說,就是依藍戴盆地持有悼環的事實。
現在,依藍戴面對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就是南方大陸以麥威兮為首的諸國國民。他們不斷傳出盆地有多小多弱的雜音,擺出軍國主義的態勢。瓦爾倫斯建置了被動防禦的方案,不過瓦對於他如何贏得這些功勳獎章仍抱持疑問。就瓦至今的了解,新組建的軍隊仍然沒有見識過任何實際遭遇戰。
第二個問題就離自家更近了。首都外但仍在盆地範圍的地區,人們概略囊括稱為外市(the Outer Cities)。數年來,也許數十年來,依藍戴市與其他所有城市間的緊張逐漸產生。
面對另一片大陸的威脅已然夠糟。但對於瓦而言,那是天邊的危險。立即的一個,給他最多壓力的一個,反而是在他們自己人間發生內戰的前景。他與史特芮絲數年來就是在努力避免這個。
瓦爾倫斯終於向他的副總督點頭致意,那是一名泰瑞司女人。她有深色鬈髮與傳統長袍。瓦覺得他應該在村莊時與這人相識,但也可能是她的姊妹,而他一直不知道要如何開口詢問。不論如何,有個泰瑞司人辦事看起來就體面。大多數總督都會指派一位到內閣的高階職位——彷彿泰瑞司人是某種炫耀用的獎章一樣。
雅達瓦順(Adawathwyn)起立向房內宣告:「總督請拉德利安家族的參議員發言。」
雖然早就在等待此刻,瓦還是用他的時間漫步踏上演講臺,該處已被上方巨大的電氣聚光燈照亮。他緩緩環視,審視整個環形議堂。一側是民選官員:被票選進政府來代表公會、職業或歷史團體的參議員。另一側是貴族領主:因為血統的優勢而把持現在位置的參議員。
「這個法案,」瓦向會場宣告,大聲且堅定,迴盪於廳堂。「是極其愚蠢的想法。」曾經,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直言不諱只為他引怒火上身。但現在他看到參議院的多名成員露出微笑。他們已經習慣——甚至還讚賞。他們知道盆地裡有多少問題,也樂見有人願出聲。
怒火:此處原文用字是 ire
「與麥威兮的張力已經在歷史最高點了。」瓦說。「是時候讓盆地聯合起來,而不是挑播離間各市!」
「這就是聯合!」另一個聲音呼喊。碼頭工人的參議員梅爾司風(Melstrom)。他幾乎就是一具海斯丁與艾瑞凱的傀儡,貴族長年安插在瓦旁的尖刺。「我們整個盆地就應該只有一名領導者。理應入法!」
「我同意,」瓦說。「但依藍戴總督——一個城市外的人們不能為其投票的職位——又如何能聯合群眾?」
「這能給他們景仰的目標。一個強而有力的能幹領導。」
那傢伙,瓦瞥一眼瓦爾倫斯想著,是個能幹領導?如果他能在會議上投注比造勢行程更多的關注了話我們就謝天謝地了。瓦爾倫斯這人,在任期至今的兩年裡,政績就是重新整建了市裡的十七座公園。他喜歡花。
瓦按照計畫,掏出他的獎章拋到空中。「六年前,」他說。「我有一場小小歷險。你們都知道。找到一艘損毀的麥威兮飛船,挫敗外市打算用其祕密來對抗依藍戴的陰謀。我阻止的。我還帶悼環回來安全儲藏。」
「然後幾乎挑起一場戰爭,」某人在房間彼方咕噥。
「你比較希望我讓陰謀繼續成長嗎?」瓦反問道。他一邊等待著不會來的回答,一邊再繼續拋接著獎章。那是一枚麥威兮使他們的船變輕得以飛行的重量獎章。「敢問此處各位誰能質疑我對依藍戴的忠誠?我們可以來場友善的小小決鬥。我甚至可以讓你先射擊。」
沉默。這是他掙得的。這房間裡的很多人不喜歡他,但他們確實尊重他。他們知道他不會是外市的特務。
他拋出獎章並推得更高,直到上方挑高的天花板。它再次下墜,閃耀微光。當他接住時,他瞥一眼現任麥威兮國大使約妮絲(Jonnes)海軍上將。她坐在參議院的特別席,與外市市長拜訪時列席的位置相同。沒有一個市長參與會議。他們憤怒的明顯象徵。
這個法案,如果通過了,將會提升依藍戴總督的地位在所有外市市長之上——使其得以干涉當地爭執。甚至得以罷免市長、發起補選、提名候選人。雖然瓦同意一個中央統御者是聯合盆地重要的一步,但這個法案是對於首都之外所有人民權利的公然漠視。
「我清楚我們的處境,」瓦說,在指尖轉動著獎章。「比任何人都清楚。你們想要向麥威兮展示武力。證明我們可以使我們自己的城市屈服於我們治下。所以你們引進了這個法案。
「但這更強調了為什麼依藍戴外的所有人都如此反對我們!其他城市的革命若沒有人民支持將無法持續。若非生活於依藍戴外的普羅百姓都如此深刻地惱怒於我們的貿易政策與舉手投足間的傲慢,我們不會落入如此處境。
「這個法案不能平息民意!不應該『展示武力』。這刻意設計來激怒人民。如果我們通過法律,我們就是追求一場內戰。」
他讓眾人沉澱一下了解主張。其他人如此執著於強兵政策抵禦外敵。但若有所不慎,他們的兵刃將會投入內部爭執引起的戰爭。麥威兮是個問題沒錯,但不急迫。然而,內戰,迫在眉睫。
最糟的是,有人還在暗中推動。瓦相當確定集合再次插手依藍戴政治。他的……姊姊也涉入其中。他不確定為什麼他們想要一場內戰,但他們肯定已經準備數年了。如果讓這個通過,落入真正大敵的手掌心,他周遭的菁英與外城的革命將會共同造成一場哀悼。
瓦從左側口袋拉出一疊紙。他把貓狗圖畫塞回去,然後把其他的向房內展示。「我這裡有六封外市政治人物的書信。他們代表一個不想要衝突的大派系。這些都是可以溝通的人。他們願意——也渴望——與依藍戴共事。但若我們繼續強行施加帝國主義暴政於他們身上,他們也懼怕他們的民意。
「我提議我們否決掉這個法案重新擬定一個更加完善的法案。一個確實有助於和平與聯合的法案。有著國民大會以及各外城代表,以及一個由那個群體選出的最高政府。」
他預期噓聲,他也得到一些。但廳堂中大多數還是沉默,看著他高舉書信。他們害怕讓權力從首都流失。害怕外市政治將改變文化。他們是懦夫。
也許他也是,因為集合從中牽線的徵兆而被嚇壞了。現在這些盯著他的人之中誰是他們的祕密特務?鐵鏽的,他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動機。他們想要戰爭——來奪取權力,這很顯然。但不只如此。
他們追隨一個叫做特雷的信仰。
瓦緩緩轉身環顧,繼續舉著書信,並在背向梅爾司風時感覺有如尖刺在背。他打算開槍了。瓦心想。
「拉德利安大人,恕我直言,」梅爾司風說。「你是一個新手家長,而且顯然不知道如何養大孩子。你不能讓他們予取予求,你要硬起心腸,做出對他們最好的選擇。他們最終總會明白苦心。而父親對於子嗣的關係,就是依藍戴對於外市的關係寫照。」
就在正後方。瓦心想,並一邊轉過身。
他沒有立即回應。你會想要小心地瞄準再回擊。他先前曾經向房內許多參議員發表過這個論點了——大多數都是於私下拜會時進行。他正在取得進展,但他需要更多時間。有了這些書信,他可以再度拜訪每個還在牆頭觀望的參議員,並傳播言論。改變想法。乃至於勸服。
他的直覺告訴他如果今天進行投票,法案會通過。所以,他來此並非為了重複他的論點。他是帶著一顆上膛的子彈來的,準備發難動手。
他折起書信緊塞入口袋深處。然後從另一個口袋拿出較小的一疊紙,只有兩張。就是史特芮絲怕他忘記而準備的備用。她可能也為其他幾疊文件準備了副本。還有其他七份她知道他用不到的東西也是——不過那些東西在袋子裡以防萬一能讓她安心一點。鐵鏽的,與那名女性相處令人愉快。
瓦握住紙張並做出彷彿光線強度只勉強夠讀出來的表演。「『梅爾司風議員鈞鑒:』」他大聲讀出來,「『敝家族樂見足下願意看清時勢並繼續維護依藍戴貿易業在盆地裡的優勢。敝家族將交付未來三年航運收益的千分之五以換取足下對於此法案的支持。海斯丁一族 同 艾瑞凱一族 耑此』」
房內混沌爆發。瓦安頓下來,手指勾在槍帶上,等待狂怒的呼喊傳過來。當梅爾司風倒回座位中時瓦對上他的眼睛。鐵鏽的白癡剛學到重要的一課:當你的政治對手是受訓偵探時別留下貪汙行跡的紙本資料。白癡。
當喊叫終於止息時,瓦再次開口,且更加宏亮。「我要求我們舉行瀆職聽證會以調查梅爾司風參議員公然違反反貪汙法的明顯賣票行徑。」
「然後因此緣故,」總督說。「推遲依藍戴優位法案(Elendel Supremacy Bill)投票?」
「怎麼可能投票?」瓦說。「我們都不能確認票是不是在善意忠實下投出的。」
更多狂怒。總督與副總督討論的同時瓦等候著結果。她是聰明人。瓦爾倫斯的作為中所有不涉及剪綵或親吻嬰兒的恐怕背後都有她的出力。
當廳堂冷靜下來時,總督看著瓦。「拉德利安,我相信你有著這封書信可信度的證明。」
「我有三名各自作業的字跡專家的證詞,證明其並非偽造。」瓦說。「我妻子對於書信取得的詳盡記述也全面且無可抨擊。」
「那麼我建議隨後舉行瀆職聽證會。」總督說。「此前先進行優位法案投票。」
「但——」瓦說。
「我們將會,」總督打斷瓦的話,「令梅爾司風、海斯丁和艾瑞凱排除於投票之外。確保投票不受賄選影響。」
該死的。
該死的,該死的,該死的。
在他得以反擊前,副總督敲敲她的主席槌:「是否贊成投票繼續進行?」
參議院大多數的手都舉起了。對於像這樣的簡易投票,會採用更粗糙的投票方式——除非票數非常接近。但現在並沒有。
這個法案,正式的投票,將緊接進行。
「拉德利安,你還有要投放什麼爆炸性消息嗎?」總督說。「不然我們就繼續?」
「閣下,沒有爆炸了。」瓦嘆氣說。「那是我老伙伴的專長。我只想對議堂做最後的懇求。」他的計謀失敗了。現在他要打出最後一張底牌。不是瓦希黎恩.拉德利安的請求。
而是執法者曉擊的。
「你們都認識我。」他說,並轉了一圈,對上他們的眼睛。「我是從蠻橫區來的簡單的人。我政治玩不好,但我真懂憤怒的人民與藍領工人的艱苦生活。
「如果我們視自己為家長,那我們應該善待我們的孩子。給他們為自己發聲的機會。如果我們繼續假裝他們是幼兒,他們將會無視我們——而且這還是最好的情況。你們想要傳達一個訊號?傳達給那些我們在乎且願意聽的人吧。」
他最終回座坐定,就在楊西.亞切奇科(Yancey Yaceczko)旁,他是個好脾氣又耐心的傢伙——也是幾個會確實聽進瓦的話的參議員之一。
「好演說啊,瓦。」那男人傾身低語。「真的是一場好演講。總是樂見這樣的東西。」
楊西會支持他。事實上,有相當人數的貴族與瓦有共鳴。當瑪拉席近期說的很多事物開始讓瓦對其世襲地位不安的同時,這個情勢也讓領主們可能試著比競爭對手稍微收斂一點貪汙行徑。民選參議員必須要保住席位,因此會支持這個可能會改善選民生計的法案。
這是個問題。根據最新的普查,現在生活在市外的人比市內的人多。而大多數法律都要追溯回只有一個城市其他都是農村的那個時期。現在那些村莊也成長為城市,他們的人民想要在盆地政治裡有更大的話語權。
依藍戴不再是末日後重建的散亂聚落。他們成為國家,即使蠻橫區也在改變、成長、現代化。鐵鏽的,考慮上蠻橫區的所有土地,他能想像總有一日居住在那裡的人將比整個盆地適居人數還要多。
他們需要給予那些人選舉權,而不是無視他們。他仍然抱有希望。他、史特芮絲與他們的盟友數個月來致力於瓦解對法案的支持。無數的晚餐、聚會,甚至還有如他開始為城裡某些菁英所做的一樣——在射擊場的訓練活動。
全部都是為了改變世界。一瞬間的一張票。
總督要求進行投票,蜜雪兒.尤門貴女投出了第一票——反對法案。隨著進行,瓦坐著,有如與強盜團決戰前夕的焦慮。鐵鏽的……這其實更糟糕。每一票都是一顆出膛子彈。富菈(Faula)貴女與紋戴爾(Vindel)參議員。他們會出爾反爾嗎?瑪菈亞(Maraya)呢?她是被說服了,抑或……
富菈 Faula:在加泰羅尼亞語與奧克語中意思是「寓言」,源自拉丁文 fābula
他們中有兩個支持法案,加入他們的還有多名瓦一直不太確定立場的議員。隨著投票進行,瓦心情逐漸低沉,感覺比被射中還糟糕,而票數最終定格在 122 票支持,118 票反對。
法案通過。他的胃更沉了。如果瓦打算阻止內戰,他需要找出另一個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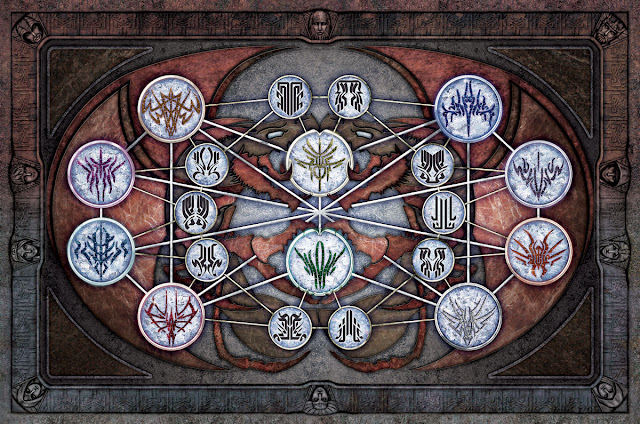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